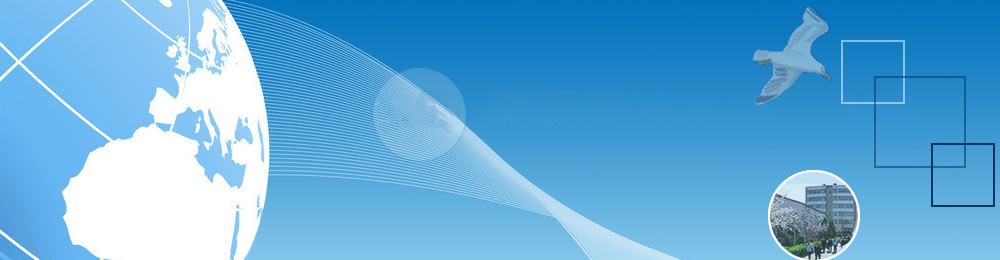几十年、上百年过后,人们会在历史书里这样记载:大疫情前,如何如何,大疫情后,如何如何。疫情前后将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就如同这些彼此隔离的日子,你的朋友圈里,那么多的朋友,让你突然感到如此陌生......
接下来的日子,我们需要从精神和物质上同时做好准备,以迎接一个不一样的时代:去全球化,国家和民族主义盛行,信任成本越来越高,不同文化的对话越来越困难;市场经济收缩,消费主义基础削弱,精致的现代经济体变得粗糙,线上经济、距离经济、非接触经济成为新潮;城市化不会再高歌猛进,回归乡土和安全,重寻信仰和反思存在,新实用主义泛滥;后现代的随性、无厘头、无规则将被传统的集体秩序淹没,病毒在制造新的人际、国际交往关系,空间和距离变得异常重要,人们更信任血缘相同的族群,现代型的社会将因为疫情被再次解构;如何定义“戴口罩的人”,将成为存在主义新的哲学命题......
一、大疫情塑造的历史:现代性的再次解构?
史无前例的大疫情还在进行中,已经有学者迫不及待的构建叙事话语。他们将“新冠疫情”称为历史的分水岭,如同人们在叙述近现代历史时,一般将“二战前”和“二战后”分为截然不同的两个阶段。所以接下来的叙事习惯里,将会有“新冠疫情前”和“新冠疫情后”这样的区分。
当一切成为历史的时候,时代的断层线才会“泾渭分明”。也不用感叹这么多的“活久见”,人类社会从来就是如此。只是因为你此前所处的时代,岁月静好的太久。
命运的走向总是悄然变化,转折点只是书写在大历史中。身在其中的人们,往往具有先天的钝感,这或许是一种保护,否则每天置于宏大动荡中,渺小的个体该如何承受。但这个蔓延全球的病毒,所产生的影响如此之巨大,足以作为历史叙述中的标志性词汇。虽然,它只是加速了时代的剧变——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大变局。这些影响的确是声势浩大、立竿见影,比如疫情带来的伤病死亡、经济停摆和金融动荡,这些变化如同战争一样实实在在。而另外一些变化,深远的、潜移默化在时代记忆里的,隐藏在长波周期和文化意识里,悄悄的为时代注脚,然后有一天突然走上历史舞台,成为主角。
从某一个角度来说,人类历史是由灾难塑造的,瘟疫可以改变社会和政治形态的演变进程,《瘟疫与人》对此有系统的研究,比如大瘟疫与极权政治、宗教禁忌、社会等级等,有着密切的关系。大型动物的死亡,人口数量的增加,促使人类进入人口密度更高的农业社会,从此瘟疫就如影随形——这种看不见的病毒,在显微镜诞生之前,在古时代是神秘和鬼魅的。从生态学来说,这是在人类进入生物链金字塔后,大自然的一种平衡方式。这也是马尔萨斯陷阱的逻辑。而无论是雅典大瘟疫改变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局势,还是古罗马大瘟疫改变的帝国运数,谁也说不清究竟这是历史的偶然还是必然。
十四世纪的欧洲黑死病造成了超过1/3人口的死亡(大不列颠地区死亡了一半),导致劳动力奇缺,三分之一的土地无人耕种,人力成本陡升,租赁制替代农奴制,为圈地运动以及之后的工业革命埋下了伏笔(劳动力奇缺倒逼资本形成);而大量天主教神父和其他教职人员的死亡,只能让年轻的教徒匆忙补缺,这些人大部分并不像以前的神职人员那么虔诚,旧传统和公共礼拜仪式的衰微,这也可能埋下了两个世纪后宗教革命和文艺复兴的种子(见[英]弗朗西斯·艾丹·加斯凯,《黑死病——大灾难、大死亡与大萧条》第10章)。而这些,又集体构成了现代性的开端。
灾难或危机塑造历史的逻辑,有点像社会达尔文主义,一个没有人性温度和人文关怀的强权论和宿命论(木心说超人哲学不可说)。的确存在这么一个规律,存亡兴衰,王朝更迭,在大历史的时间线上合合分分、起起伏伏。每一次大的灾难,无论是战争还是自然灾害,在毁灭和制造悲剧的同时,也在孕育着新生。亚里士多德说战争是万物之母,尼采说悲剧诞生后,超人赋予大地以意义,灾难正在塑造强人意志。二战之后,无论是工业文明(计算机,网络和新能源),还是制度文明(全球秩序、独立运动和民主化浪潮),都可以溯源到战争和灾难的“赐予”。也是从二战之后,人的后现代性变得更加突出。
大瘟疫或许只是一个巨大的导火索,加速了一个时代的结束——自二战以来形成的全球化政治经济秩序。这个论断可能有点大,但是我冒险做出这个论断。以科技为豪的现代人,自以为走出马尔萨斯陷阱的现代人,没想到在一个看不见的病毒面前如此无能为力。人们必须告别,不管是暂时的还是漫长的,必须告别代表后现代性的生活方式——结束夸张表达,戴上口罩千篇一律;结束社交狂欢,人与人之间必须保持距离;结束狂热的自由主义和消费主义,回归森严的战时秩序和沉默的隔离空间,回归与自我的相处与和解,回归家庭和陪伴,回归古典和朴素。乐观的说,是回归海德格尔式的诗意栖居的空间,回归诗与思的世界。
而代表后现代主义的物质景观,天上飞的、地下跑的,也暂时安息:一切仿佛回到了太初,回到旷野的宗教寂静里。当后现代的人类开始隐居的时候,大地开始呈现出意义。据科学家统计,在人类经济活动停摆的几个月里,因温室效应造成的温度上升竟然有所缓解,空气和水的质量明显变好。令人吃惊的是,近半个世纪因空气污染看不到蔚蓝天空的印度,突然有一天在远方看到了从没看到过的喜马拉雅山!这种神谕式的图景,究竟意味或预言或警示着什么?作为现代后现代的工业人、科技人、经济人,是被什么蒙蔽了眼睛和心灵?这样的存在主义拷问,可能就是大疫情作为历史分水岭的心智基础。疫情越是迟迟不消散,或者反复出现,这样的问题就越是逃脱不开,最终也就导致了疫情前、疫情后的历史分野。
二、大疫情前后的割裂与对立:时代的清算?
不管承认不承认,愿意不愿意,或者说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一个时代过去了。自二战以来的历史运数上升期,到今天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并不是说运数衰落,而是要进入一个碰撞、冲突和纷乱的“三国时代”。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新旧力量需要在较量中实现新的博弈均衡格局,而相对于看得见的,看不见的才是真正的决定性力量。大动荡的时代,是再平衡的时代。
二战之后,有四股潮流在全球兴起,浩浩荡荡,顺者昌逆者亡,分别是:
1)工业化。二战后,无论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还是东方社会主义国家,工业化成为战争后国家的第一主题(中国建国后的重大任务是工业赶超英美)。发生了两波工业革命,电气革命基础上的第三次和第四次工业化浪潮,现在处于第四次的信息化浪潮中。工业化无关体制,前苏联的计划体制,在一段时间内曾实现了巨大的工业化成就,但终究在第三波和第四波工业化浪潮的交接时期走向崩溃。中国也在改革开放后真正引爆工业革命,现在处于旧的重工业产能出清和新一轮产业升级的叠加进程中(见赵建,《中国的工业革命》,《经济研究参考》,2019年第6期)。可见,市场经济才是推动工业化的基本力量,但在特殊历史条件下,不能忽视计划体制下的国家动员能力。
2)全球化。战争重塑权力格局,世界大战重塑全球权力格局。二战后,建立在《雅尔塔体系》上的全球秩序形成,联合国,世界银行,IMF,关贸总协定及以后更加普世的WTO,解决全球公共卫生问题的WHO,以及近几十年为解决金融危机、气候变暖等共同问题的各种全球治理框架(比如巴塞尔协议),G20等。在这些全球秩序构建的基础设施上,各国经济贸易往来日益频繁,产业链和供应链在全球化基础上变得更加细分、精致和复杂,经济效率大大提升,开放式经济体的形成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长的低通胀、高增长时代之一。地球变得越来越像一个村落(地球村),移民、跨国公司、留学、国际旅游等成为风尚,文化产品也在全球流行、兜售。在这样的大趋势中,民族的、国家的,与普世的、国际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碰撞,虽然无时无刻,但都被大浪潮所掩盖。不同种族、国家和地区的人们之间变得更加友好、宽容和开放。
3)民主化。迄今为止,民主化经历了三个“长波”,第一次民主化长波:1828年-1926年,起源于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第二次民主化短波:1943年-1962年,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三波民主化:始于1974年葡萄牙康乃馨革命,最高潮是苏联的解体,及众多国家的传统体制的解体,“国王”们被送上法庭或尸横街头。然而最近几十年,据民主之家的统计,民主化浪潮有退潮之势,民主国家的数量在减少,取而代之的是更加流行的“强人政治”(普京式)。用福山的政治理论来说是“民主政治的衰退”。
4)现代化。现代化、现代性是一个更加泛化的定义。二战之后,建立现代型社会,在各个层面实现现代化,是各国普遍的目标。更深一层的则是,欧洲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以来的现代性反思,19世纪末以来对现代性的解构和后现代性的建立。社会科学上的方法论个人主义,人的价值的重新确立,自由主义和注重表达自我,现代性深刻的改变了人文社会景观。然而19世纪末以来,对理性的质疑和存在的迷茫,无厘头、虚无主义的泛滥,对现代性解构以后,后现代没有完全重构世界。当传统的形而上学二元结构被尼采颠倒,对存在的思考开始胜过本体,只有在者言说存在,思和诗的授予性复兴第一哲学,语言作为经典哲学中的形式反而成为存在本身(词语破碎处没有存在,海德格尔)。后现代性解构了一切,虚无主义无时无刻不在侵蚀着人的精神世界。弗兰克尔说从后现代的艺术作品里(抽象派、野兽派类似幼儿涂鸦,重金属摇滚乐的嘶吼),看到了人类精神世界的失落、迷茫与堕落(弗兰克尔,《乌托邦与悲剧》)。既然遗失了本体和彼岸,人们只能在狂热的消费主义,购物节,狂欢节,金融对赌,资产泡沫一夜暴富的物质幻觉中,找回短暂的“存在感”。与每隔一段时间出现的金融、经济危机相比,现代人的精神危机一直都存在。
正是这四股趋势,塑造了今日之世界。然而最近几年,确切的说应该是从美国次贷危机之后(金融民粹主义泡沫的一次破灭),趋势就正在发生变化。巧合的是,美国特朗普上台和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开启(惊讶于同时),加速了拐点的到来,直到疫情的爆发,历史的巨变正式显现。如果上面的四股浪潮是疫情前的世界,疫情后的世界将大不相同:
1)虽然信息革命、数字革命的工业化仍在推进,但核心的矛盾是上一轮工业化浪潮的清算,即过剩产能和过高杠杆的出清。历史经验表明,每次新旧工业化浪潮或康波的交接时期,都容易发生历史大动荡。疫情过后,过剩的旧产能如何消化和输出,过剩的债务如何化解,为拯救经济推行的货币大宽松如何转嫁,是各国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从1929年大萧条的历史经验看,以邻为壑,重商主义,国家间摩擦,甚至是用战争来解决过剩产能的极端情形,为现在发生的事态走向提供了线索。我们不认为这次危机会像大萧条那样严重,但是在各国竞相用债务刺激国内经济,竞相转移过剩产能的过程中,不排除偶然的全球极端事件发生。
2)全球化加速退潮,除了客观上疫情原因导致的全球供应链断裂外,各国之间因疫情发生的文化撕裂和意识形态间隙,正在导致进一步的去全球化。人们惊讶的发现,在看不见的病毒面前,全球产业链和各国关系如此脆弱,国家友谊看上去地久天长,实则不堪一击。而疫情爆发后,各国深陷危机,本来这个共同问题需要全球共同面对,可惜的不是各国之间的并肩作战和同仇敌忾,而是互相埋怨和指责。拿美国来说,过去普世价值体系下对人类终极命运关怀的大国气度荡然无存,剩下的只是国家主义和沙文主义。撤侨、封国等隔离举措在全球的运用,背后是升腾的国家、民族甚至是种族戾气。而文明之间的隔空对话,鸡同鸭讲,又进一步加重了这个隔阂。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半个多世纪全球化带来的问题和矛盾,已经积重难返:贸易失衡、环境污染、贫富分化、意识形态矛盾等等,才会导致疫情这样的全球灾难发生后,各国关系出现了逆向选择,不是合作,而是割裂,转嫁矛盾。
3)疫情爆发后,人们可能不再用是否民主来评价一个政治体系,而是更加看重国家能力和实际治理成效。这在中国得到了较好的证明,14亿人口的大国,竟然能在两个月内将疫情控制住,充分利用大国优势集中支援重灾区,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当然也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但总体来看值得肯定。另一个角度,用主流的政治学思想来评定,民主也可以塑造更加持久的国家能力,虽然其广受诟病的权力制衡和否决政治,对处理疫情这个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看上去缺乏效率,但是到最后仍然可以表现出充分动员社会、社区、市场等非政府资源的分布式、自组织能力。然而,这次疫情的影响太过猛烈,深深的烙在各国的集体记忆里,从而产生更多的对集体主义和国家能力的依赖。因为与民主相比,这些能带来更加实在的安全感。而且,21世纪以来民主化的退潮,在这次疫情过后可能更加加速。美国的特朗普现象更多的是代表“民粹主义”,桑德斯虽然退出,但是他的选票令人吃惊的显示了美国人对社会主义的热情。在衰退的政治能力面前,民众可能更加需要强人政治(新加坡模式的泛滥?)。
4)现代性将被再次解构,“戴口罩的人”将成为存在主义诗与思的新主题。这代表着什么,在狭小的隔离空间里,现代人将如何重新定义存在?如果人与人之间不能聚集,城市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如果所有的活动搬到了线上,虚拟世界是否对现实世界进行全面的接管,庄周梦蝶的自我质疑将不断萦绕在现代人的心头?在瘟疫笼罩的城市上空,后现代主义如何呈现自己的个性张扬与无厘头?末日狂欢还是重回田园?重新学会与自己相处,是现代人面临的又一次重大抉择,也是对过度消费、过度自我消耗时代的一次“大清算”。
三、疫情新常态与债务型经济:带病生存的金融世界
如果疫情长期存在或者不定期爆发,本已脆弱的债务型经济该如何存续?
对经济学的研究来说,一般在描述大的事件冲击时应尽量保持克制——宏大叙事是语言和逻辑的双重加杠杆,虽然也有必要,但容易走向复杂现实过度线性化的危险(民科现象)。同时也要坚持熊彼特的“边界分析法则”,即在解释一个经济学现象时,不断层层解析,直到触碰到非经济学解释,无论是政治学、社会学,还是历史学、心理学,才算穷尽经济学框架的边界,不再是“用现象解释现象”、“用问题转移问题”的语意重复与逻辑取巧。
面对疫情,经济学的思想库和工具箱并不匮乏,卫生经济学早已建立成熟的范式,传染病或疫情经济学算是一个分支。但是,面对这一次史无前例的大疫情,传统的卫生经济学显得捉襟见肘、力不从心了——它既无法完全解释疫情发生的前因后果(当然这可能不在其研究范围),冲击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也无法预测疫情对人类命运的改变。单纯的经济学,如果缺乏对历史和社会学的洞察,将无法回答新冠疫情何以成为历史分水岭。
这促使我们冒险拓展分析范式,“野心勃勃”的构建一个更大的动态系统,将更多的外生变量内生化。这个范式拓展的冒险之处在于,所构建的逻辑更多的是基于有限事实基础上的思想实验,很难进行“科学范式”下的假设检验。但是,这个缺憾并不能阻止我以假说或猜想的形式提供某个视角的观察。事实上,就连为经济学科学提供实验方法而诞生的计量经济学,也无法提供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式证伪”。否则,经济学就不会有如此多的思潮纷争。
范式的转换并无太大的特别之处,可以说是经济学帝国主义在结构上的拓展,建立一个将诸多外生变量内生化的大系统。这在技术上是令人绝望的,尤其是对习惯于求均衡解或稳态路径的经典经济学模型来说。假如这个范式将瘟疫等自然灾害,看做是债务型经济的内生冲击,是经济本在不稳定的另一种形式,那肯定会引来巨大的质疑——在经济与自然灾难之间,是否存在一种神秘主义的玄学逻辑?
答案或许依然在经典的经济学系统论范式之内——新冠疫情也将可能成为经济史的分水岭,因为它终结的是长达半个世纪的超级债务周期,以及这个周期中制造合成“人工债务病毒”的始作俑者——超级央行(大量的有毒资产附着在央行的资产负债表上)。其中的逻辑脉络沿着以下展开:
1)经济系统运行摩擦产生的熵增,并不会凭空消解,它会不断累积或者向其它子系统转移。这或许可以表述为“风险守恒定律”,除非产生新的“创造性破坏”,通过提高潜在生产率来产生熵减(能量),消解掉过去累积的熵增。我之前的一篇学术论文《中国经济波动被“熨平”了吗?——现象、机理与影响》,提出了这种可能的转移机制,那就是:
2)由于逆周期政策和国家金融能力的不断强化,一旦经济发生危机,政府就会采用金融工具进行对冲,最终导致经济体系的波动不断向金融体系转移。这是“金融是现代经济核心”的一个脚注,也就是金融体系成为了现代经济波动的一个重要缓释工具。金融加速器既放大了波动,同时国家金融资本的干预又承载了波动——不过是将宏观风险成本向未来摊销。然而:
3)在不断解决经济危机及金融危机的过程中,金融资本在国家的不断赋权下,具有了强大的自发性和自组织能力(脱离实体)。它以系统性风险绑架了以央行为代表的公共资源,也将金融和财政绑架在了一起,大而不能倒的金融机构越来越多,从国家刚性兑付中获利的道德风险成为一个系统性的大宏观问题。从某种意义上,央行已经成为金融集团的“最后贷款人”,“最后交易商”,以及音乐停止后的“最后买单人”。金融资本主义成为一种更加隐秘的掠夺工具,它在制造风险的同时,也在制造业史无前例的两极分化、金融托拉斯、相对贫困和国家及阶层间冲突,这就导致更大的风险转移:
4)如果国家意志总是人为干预不允许金融风险出清,不允许总量危机,那么不断积累的结构问题将引发结构危机。结构性危机无法用传统的总量政策工具解决,危机最终会在非经济和金融领域爆发,此时将会发生重大的范式变迁,即金融风险异化为外部冲击(战争、动乱、瘟疫等),回过头来反噬经济金融系统。在此范式下:
5)传染病毒也可以看作是金融和经济无法出清,自然生态资源通过病毒来进行再平衡的过程。《瘟疫和人》中用翔实的史料佐证了几万年来自然生态这种平衡机制的存在。即使病毒是人工合成的,那也是结构性危机引发的社会病态,这就重新回到了4)的论证。其实也没有那么玄学,只要将自然生态看作是与土地、石油等类似的基础资源,一切就可以在经典的经济学模型中做出解释。与石油和土地相似,如果短期内攫取过度,生态资源也具有不可再生性(来不及消化)。生态资源的衰竭就是气候的变化,地震、山火、虫灾,瘟疫等出现,以抵抗人类过度亢奋的经济攫取。而人为制造的超级债务周期,就是一直在制造这种过度攫取——经济危机本来是让自然生态自我修复,但是人为制造的超级债务周期阻止了这种自我修复,所以也就有这样的终局。
如果没有疫情,债务型经济或许可能一直持续下去,美国的股市和中国的房地产,也可能一直涨下去。疫情爆发之后,被赋予超级货币发行能力的央行,会再想尽办法将病毒制造的经济衰退风险转移到金融领域,继续用总量来掩盖结构危机。不到一个月,美联储已经扩表40%,表外更加的庞大,接近无限的救济。但已经江郎才尽的央行,在疫情造成的经济断裂带,并无法立即带来弥合和治愈。她所能做的,只是延缓危机的发生,并将小危机积累成大危机。未来的金融世界将是什么景观?在我们新构建的包括生态资源的新范式里,最好的答案应该像日本,或者其它一些宗教国家,资产负债表幻灭引发的长期大衰退,在社会文化层面引发了极简主义、断舍离、宅文化等最大化节约生态资源的模式,以及出生率的下降和总人口的减少(这个未免残酷)。对于一国的经济来说,这恐怕是个噩梦,但对于大的生态系统来说,这可能是大自然天地不仁以再平衡人与自然关系最温和的方式之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