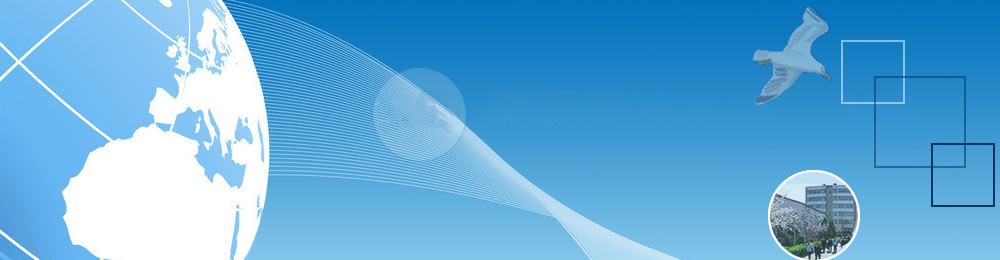本文根据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比吉特·班纳吉和许成钢教授在2019年11月9日“财新峰会”上的对话整理而成。
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比较”(comparative-studies)
许成钢:我首先介绍阿比吉特·班纳吉。他是我的高年级同学,是一位杰出的经济学家。在他学术生涯的早期,在理论经济学方面做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后来,他的研究领域有了重大转变,从纯理论经济学家转变为从事实验的发展经济学家。他目前的研究重点是贫困与不平等,这些是包括发展经济学在内的经济学中最基本的问题。为什么有些国家在发展,有些国家却裹足不前?还有政策问题:为什么一些主要政策不成功?我们应如何设计政策,如何审查政策?班纳吉教授的重要贡献包括经济增长与发展、不平等与贫困、教育与发展等基本理论。他获得诺贝尔奖的重要贡献之一是方法论,特别是随机对照实验(RCT)。他将随机对照实验这一在医学临床研究中行之有效的方法,应用到经济学中。现在,我将与班纳吉教授进行对话。
我想根据你的案例提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你表示疟疾死亡率已经大幅下降。我们能再多了解一点吗?是什么原因,或者说是什么因素促成了这种稳步下降?
班纳吉:我想我已经做过解释,但我肯定说得不够清楚。我认为最大的一个因素是用杀虫剂处理过的蚊帐的价格大幅下降。这一技术是众所周知的。多年来人们已经知道,让孩子睡在用杀虫剂处理过的蚊帐里,蚊子会死亡,孩子则不会感染疟疾。这早就不是新鲜事。
不幸的是,人们觉得这种蚊帐很贵,承担不起,因此都不使用。于是,在我亲爱的同事、斯坦福大学教授帕斯卡琳·达帕斯(Pascaline Dupas)的鼓励下,政府降低了此类蚊帐的价格。她在一系列实验中表明,降低价格确实提高了儿童使用蚊帐的比率。降价遭到诸多阻力,因为有一个普遍的理论认为,如果降价,人们就不会尊重他们得到的东西。如果蚊帐降价,他们只会滥用蚊帐。
事实上,为了验证这一点,她不得不在晚上派人去检查孩子们是否睡在蚊帐里。如果他们睡在蚊帐里,就不会感染疟疾。事情就这么简单!正是降低蚊帐的价格导致了疟疾的减少,而这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达帕斯提出的证据。
许成钢:非常好!我的下一个问题有关实证工作的方法论,尤其是随机对照实验方法。这个方法在医学临床研究中已经并不新颖,但将其引入社会科学却是创新。将随机对照实验从医学临床转变到社会科学问题,研究对象和环境都有巨大的改变,我想知道,其中的主要挑战是什么?
班纳吉:我认为有两个挑战:挑战之一是遵从率。在一项医学实验中,譬如有70人,其中35人服用一种药丸,另外35人服用另一种药丸,大家照此行事。他们每周都来,通常都是病情严重的人,所以他们有很强的动力参与。
在社会科学实验中,你知道,我们经常有300万人。他们中的一小部分实际上会直接受到干预的影响,但我们不知道他们是谁。我们可以在村庄做实验,选择一些村庄,对它们干预,而对其他的村庄不干预。在被选中进行干预的村庄里,可能有10%的人口受到干预的影响,其余的则不受影响。我们使用大量的样本,以确保能够实际检测到这样的效果。
我们的研究里可能有一万个村庄,于是测量时必须考虑一个事实,即大多数人不会受到影响。所以,我们的随机对照实验研究在整个统计思维方式和控制方法上与医学中的随机对照实验并不相同。
许成钢:在社会科学家尝试进行随机对照实验研究时,如何能在这个实验中获得有意义的结果,这些实验的做法一定需要遵循一些隐含的假设。
第一个隐含假设是,研究者的目标应该是客观的发现,而不是有意偏向某些政策;不是取悦政府。第二个隐含假设是,研究人员以及在研究中试图设计的政策,都必须尊重穷人的基本权利。因此,要发现的内容,或想要设计的政策,都只能以受试者的自由选择为基础。
我特意阐述这两个重要问题,是因为在不同环境中,有些研究人员可能会违反这些隐含假设。我想听听你对此的回应。
班纳吉: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我认为,整个学术界都应该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我们的实验不能随心所欲,否则会造成伤害,所以“不伤害”内嵌于我们的研究之中。如今,这相当于一个基准。假设政府正在实施一个项目。这个项目或许对人们很不利,当我们对它进行评估时,并不是选择这个项目,而是说:“你们要做这个项目,我们将项目随机指派给某些人。”因此,并不是我们决定大多数事情的道德维度。政府、非政府组织和私人公司采取行动,我们通常只是安排谁参与项目谁不参与。政府规定把项目发给100个人,那么我们会尝试影响哪100人参与该项目,但并不是我们决定采取什么干预措施。也就是说,我们并不做未启动的项目,我们只是评估已经启动的项目,而不是开展我们自己的项目。当我们开展我们自己的项目时,会有意识地建立一个机构化的评估委员会,让它参与进来。我们不能做项目,更不能为所欲为。
许成钢:在你总结的五个要点中,第二个要点提到了改进而不是根本性变革。因此我想回到“根本性变革或改革”的话题上来。我想说的是,如果我们讨论的环境中已经存在私有产权,个人有选择的权利,我会同意你说的“强调根本性变革可能并不是很有用”。然而,假如在我们所处的环境中,最基本的所有权和个人选择受到限制,甚或人们完全没有私有产权,个人没有投资就业等方面的选择权。在这种情况下,赋予人们产权和选择权的根本性变革应该是非常重要的。让我再说的具体一点,在你的研究中,你强调个人选择。所以,在个人可以自由选择的地方,如果不了解穷人,我们就无法设计出有效的政策。但是,在个人根本没有产权,人们对自己做什么和不做什么没有个人选择的权利,他们必须在集体中工作。在这种情况下,赋予他们自由和产权的根本性变革,应该是重要的。实际上,这样的根本性变革才奠定了你做实验的基础。对此,你怎么看?
班纳吉: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并不是说,我关于改进而不是根本性变革的观点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正确的。我是说,的确在有些地方,根本性变革也是必须的。
在你举的例子中,请想想产权的演变过程,曾经有很多小实验,涉及很多个人的改变。我就不谈中国了,毕竟我对中国的了解不多,让我们聊聊美国的产权。产权并非一蹴而就,而是许多法院判决的结果。它始于某项法律,但随后施加了诸多限制,这些后来又被取消,法律也以不同的方式得到修订。不同时期还通过了不同的法律。《州际贸易法案》旨在限制某些财产的使用者,另外还有《谢尔曼法案》。法律上出现各种各样的变化,逐步定义什么是合法的财产所有权,什么不是。这并不是说有一种东西叫自由财产所有权,另一种东西叫非自由财产所有权。即使在最显而易见的资本主义国家,所有权也有一定的限制。这些限制可能是对的,也可能是错的,但它们随着时间演变。总之,我也认同,根本性变革是必不可少的。但我认为,在很多情况下,比如创建产权制度,实际上是逐步推进的。以美国为例,产权制度的确立也花了大约200年时间。不同的法院判决有不同的解释。有《谢尔曼法案》《州际贸易法案》等不同的法案,每一部法案都有其影响。即使在界定产权时,有没有自由产权也并非我们说了算。实际上我们总是渐进地变化,每一个变化都可以进行测试、评估,并确定它是不是好的变化。
许成钢:你们在教育与发展、教育与穷人方面做了很多研究。能简要总结一下你在这方面的主要发现吗?
班纳吉:我认为我们的研究有两个关键发现:第一个发现是消极的,即你认为会起作用的很多事情都不起作用。例如,我们可以改变班级规模,更改教科书,可以向人们提供更多教科书,给他们制作更多图表。但如果基本的教学方式错误,所有这些都不起作用。
第二个较为积极的结果是,如果你改变教学风格,就可以改进。也就是说,要因材施教,而不是齐整划一地施教,完全不管孩子能学什么、学过什么、知道什么。如果你带的是五年级的孩子,但他们不识字,那你教他们历史,他们当然什么都学不到。所以我们必须面对一个事实,即发展中国家的孩子,他们来自不同的背景,他们学习的进度不同。除非我们能适应这种速度差异并帮助孩子,否则他们无法学习。
但你若教授他需要学习的东西,他会学得很快。事实上,迎头赶上是非常快的事。
总之,我们关于教育的研究得出了两个事实。第一,如果坚持让每个孩子都学相同的课程,这行不通。第二,如果因材施教,他们会很快赶上。
许成钢:你是否可以赠送我们几句话,概述一下你对中国研究人员的建议。
班纳吉:我觉得,中国是研究质量持续迅速提升的国家之一。当前我读了很多在中国做的研究,质量相当高,进步非常快。因此,我首先要说的是祝贺你们。在过去10—15年里,中国科研人员的素质有了极大的提高。大家有目共睹,越来越多高质量的研究从中国出来。其次,我认为高质量数据的可用性,以及政府大规模项目的实施,使中国成为研究许多发展问题的一个非常有趣的地方。这种学习绝不仅仅与中国有关。